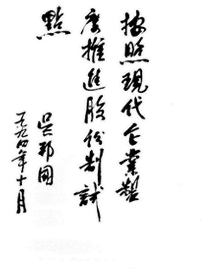被“革命”的文化
周凤珍1946年搬来后,至今住在四川南路25弄,一个有上百年历史的石库门里弄。她回忆说,那个时候的四马路(福州路)的“婊子”早已被改 造,看不见了,“陈毅来了以后,把她们解放了出来”。南京路上也常年驻扎着“好八连”——一支诞生于1947年、由一群山东翻身农民组建的、由20多名解 放军干部带领的连队。周凤珍说,“直到现在,每个月的20号,好八连都会在南京路为老百姓剃头、补鞋、磨菜刀、量血压什么的”。
而作为被好八连抵制的对象,被认为有腐蚀作用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为普通上海人与生俱来的“原罪”。易中天把上海称作“党性教育的重镇”,“据老年上海人的回忆,六、七十年代各行各业的单位里、甚至街道里弄,群众的工作和生活中的政治学习被安排得极满极多,那时候谁有胆量来谈论什么建 设本地特色的‘海派’文化?”
既然是中国商业文明最发达的城市,自然也要经受最严厉的“社会主义改造”。只不过,这改造经历了一个从和风细雨到疾风暴雨的过程。
上海协昌是一家成立于1919年的公司,由一位沈姓家族创办,中国的第一台工业用缝纫机就产自这里。现年76岁的唐振亚曾是工厂里的学徒。 1949年的大动荡中,沈姓老板选择留在上海。新政权建立的最初几年,沈老板的选择看起来是明智的,公私合营的协昌依旧生意兴隆,其生产的“蝴蝶”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最知名的缝纫机品牌,工厂为工人提供了保险和免费医疗,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这差不多也是当时整个上海的缩影——经济迅速复苏并保持 高速增长,资本家失去工厂的实际控制权但仍主导着生产和经营,中产阶级也未受牵连。
唐振亚和他当年的同事阮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真正让人感觉情况“不对了”,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之后。不仅身为副总经理的沈老板 被隔离,连唐振亚这样的技工也要被审查三代。一番折腾后,留给唐振亚一句略显矛盾的结语:无重大问题,不予培养。理由是他曾作过“资本家的学徒”。
针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清洗,则波及了几乎所有的上海市民。
上海作家叶辛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起那个时代,“小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喜欢看外国小说,聊起外国的生活方式,无意间流露出好感,被资本家出身的叔叔一把制止,‘要杀头的!’”在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的记忆里,对于上海普通人而言,革命主要是革“三包一尖”的命——比较讲究的上海男人,头上打着 金刚钻的发蜡,头是包起来的,还有包屁股的裤子,包腿的小裤脚和尖头皮鞋,都在被“革命”之列。
即便那样的形势下,上海女孩子也还是烫头发的。李天纲的小学女老师被揪住强行剃了阴阳头,一个学期没法上课。
不论男女,太紧的裤脚管也被剪掉,从裤脚一直往上剪,有的连短裤都露了出来。李天纲说自己至今记得女孩子们抱头痛哭的神情。“从那以后,好八连的针线包和草鞋成了上海的主流审美意识。”
另一个只有老上海人才心领神会的人群是“咋巴”。她们声音尖细,无论讲任何事情,声音都在四五十分贝以上。居住在宁波的上海籍知识分子施卫江概括这个群体:以低知识层次的中年女性构成,以前的身份大都是国有单位里的工人师傅,以“女大老粗”身份自居而洋洋自得于“腰背硬”,她们大都从事于服务行 业,承袭着计划经济模式的商业经营态度来服务于大众。
后来,在某些文艺作品中,这些出现在城市“窗口”的人成了上海小市民的标准照。
拥挤的,太拥挤的
70岁的上海石库门住户吴连安说,石库门原来是资本家的房子,最早只有一家人住,解放以后被收掉了,一些困难户和单位里的人被安排住进来,慢慢地就越来越挤了。
吴连安自己就是在解放初从虹口搬到了四川南路25弄的这个石库门里,他每天都要去与住处一江之隔的位于浦东的一家化工厂上班。他所住的石库门, 原来只有三层,后来房管所在楼顶加了一层,第四层的层高与下面三层明显不一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与空间的矛盾都是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矛盾之一。石库门的拥挤,是最容易看得见的表象。1950年,上海市区的居住建筑面 积总量约为2360.5万平方米,石库门里弄住宅就有1242.5万平方米,占了总量的52%以上。
但并非只有石库门才拥挤不堪。上海邮政系统的公务员任无我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起自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窘迫生活,“连石库门都没得住”。任无我那时候住在解放前新华书店留下的一个仓库里,仓库被隔成单间,改成了邮政局的单位宿舍。“我们家四口人,住20个平方(米),已经不算小 了。”
任无我住的仓库房,厨房和厕所没有单独的,十几家人共用两个水龙头。早上起来洗脸、刷牙得快点,下班得早点赶回来洗菜,不然要等到人家洗完了才能烧饭。冬天洗澡只能去单位的澡堂,一周开放一次;而在夏天,大人在家洗澡,用铅桶提水倒在脚桶里,小孩只能拿个扇子躲到马路上乘凉。
“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上海都没什么(新)房子,造个房子就是大新闻了。那时的上海就是现在的内环线 这一块,是现在上海面积的1/10,人口却是现在的一半。”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说。与此对应的数据,1949年,上海的人均居住面积是 3.89平方米。而到1979年底,将阁楼、灶间、晒台等凡能住人的面积都统计在内,也只有人均4.51平方米。人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必然带来生活习惯、社会关系的变化。
任无我谈及上海人的精打细算,“都是群体生活锻炼出来的”。他住仓库的时候,由于水表和电表也是公用的,算账就成了一门学问。十几户轮着算,每月一户主算。这并非是总用电量除以户数那么简单,谁家几个灯泡、谁家熄灯晚、无线电是否算灯泡,都是必须纳入考虑的范围。算好了贴在外面公示,大家都没有 异议时予以执行。
上海男人通常被外地人嘲笑为家庭妇男,樊卫国给出了经济学的分析:其实上海女人不希望自己的男人窝在家里操持家务,她们希望男人出去挣大钱。但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男人在工作上的努力所产生的收益对于改善家庭生活水准的作用并不明显,那么,同样的时间和精力,不如花在执掌家务上,打家具、修电 器、买菜时讨价还价。
如前所述,上海市民的生活在1949年之后不乏基本的保障,但是在改革开放前,上海人的日子也难称富足,就如同有限的居住空间一样,每每陷入捉 襟见肘之困。
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工厂里开动的机器仍为全中国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日用必需品,但轻工业的相对发达并没有提升上海市民的生活品质。
据《上海财政税务志》记载,从1959年到1978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平均占全国的15.41%,最高时达17.49%(1960年),而上 海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5%。1984年以前中央对上海的财政收入实行“统收统支”,上海每年上缴中央的财税占地方财政的87%,只剩下13%自 用。1985年以后,中央对上海财政政策调整为“核定基数、总额分成”,1988年开始实行“财政大包干”,即上海每年上缴中央105亿元基数不变,节余自用,上海上缴中央财政的比例才逐渐降了下来。据查,从建国到20世纪末,上海共上缴国家财政收入近4000 亿元,占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对此,周立波反击嘲笑上海人小家子气的外地人,“你们知道为什么只有上海有半斤的粮票吗,是因为我们收入的10斤粮票里有 9斤5两都是给了你们外省了。”
四川南路25弄在延安东路附近,它离外滩的距离只有近50米,可能是离外滩最近的石库门里弄。这里的居民谨慎而又热情,面对记者的攀谈,他们先是要求查看一下记者的证件,之后会满怀真诚地叫你“不要介意啊”,并乐于以东道主的自豪感告诉你他们所知道的一切。
“住在我们这里的人,以前大多是在附近工作的。”82岁的奚冬泉就是如此,他之前在南京路上的安康洋行做修表工作。在解放前,这是上海滩鼎鼎有 名的奢侈品店,专卖顶级生活用品,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名牌西装、皮鞋、领带、化妆品、女式服装和日用品,在这里都能找到。这里出入的都是一些留洋的年轻人和 “小开”。
上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电视剧《上海一家人》,描绘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苏北家庭。编剧黄允当时采访了黄浦、静安等商业闹市区的中小商户和上百位老人。“有的商户是百年老店、名店,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来上海学生意,吃过三年萝卜干,有的再帮师三年,以后当店员、当师傅,其中精明活络的,积点钱和朋友合伙开店,店发了,再拆股各自经营,再发了又开分店。上海人口稠密、生存空间拥挤、狭窄,也造就了他们斤斤计较、讲实惠、小家子气等习性,久而久 之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市民文化,深刻、持久地影响着上海人的心态、习俗、趣味。”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聚族而居,而上海作为商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覆盖了伦理关系,由于空间狭窄,形成了你占便宜我就得吃亏的局面,所以在个人利益上,上海人是不大讲究谦让的”,樊卫国分析说,“外地人批评上海人势利,确实存在这个现象,一个经济再窘迫的人枕头底下也要压几件笔挺的衣服, 因为摆脱了熟人社会,你走在大街上,人家也只认识你的衣服。”
上海的失落
黄金荣、国际饭店、跑马厅、大世界、大光明,旧上海十里洋场里标志性的人名和地名在奚冬泉的叙述中,有着一丝亲历者的温度。他乐意告诉你,现在的人民广场以前是跑马厅,紧挨着这里的延安东路就是原来的洋泾浜,距这里200米的城隍庙边上,原来遍布着逃荒过来的人栖身的“滚地龙”,“直到上世纪 40年代,马路上冻死的人还很常见的”。
上海人见过世面,这是真的,而他们也大多愿意向外人强调:我可是见过世面的。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计划体制和户口的壁垒加剧了地区间的差异。上海虽进行了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仍是一个特殊的城市。作为知青下放贵州19年的 上海作家叶辛举例说,上海轻工业的发达,让贵阳单位的出差者变成了拉货的驴子——每个有幸去上海出差的人,除了完成采购任务,都会受到亲友帮助购物的额外嘱托,扛回从手表到纽扣在内的大包小包。
“阿拉上海人”成了一种特殊身份,未见得比别人富庶多少,但是有自己的生活情趣,在国内有特殊的地位,被羡慕,被仰视。
上海人很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感觉不要太好哦。通常情况下,如果这句话的语境涉及自身,就不再是字面的含义,而是略带炫耀地对自己进行嘉许。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城市壁垒被部分地拆除,上海这种鹤立鸡群的城市地位带来的优越感正在逐渐淡化。对于很多上海原住民而言,心理落差尤其明显。很难相信,吴连安所住的紧靠外滩的石库门,居然是一座危房,房子下面就是黄浦江的过江隧道,地已经开始有些下陷。吴连安随手一指,楼道入口洗菜的水槽,已 经有了明显的倾斜。这原来可以算是好房子,“但现在(与)高楼一比,就是棚户区了”。
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说,国营工厂买断、大龄工人下岗,本地人在升学和就业上相对于外地精英的劣势,这些因素早已经让上海本地人在新一轮的城市扩张中急遽地边缘化。
更多元的上海,排外情绪已没那么刺眼,或者说,具备排外心理基因的人群已经被进一步的边缘化了。
1990年刚到上海生活的时候,现为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的张结海能感受到明显的“排外”。公交车售票员讲的都是上海话,当她发现乘客听不懂的时候,才改为“冷冰冰”的普通话。“现在与上海人交往,他在搞不清对方身份的情况下,都会使用普通话。”
张结海注意到一个现象——当上海严重“排外”的时候,恰是这座城市整体上陷入失落感的年代。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总结说,“过去,上海人有一种盲目的城市优越感,但现在不是GDP最大的地区了,后起的广东、浙江、江苏都在 赶上。过去讲普通话,上海人要嘲笑你是乡下人,现在反过来了,讲上海话,人家要说你没层次了。”
“大都市人的个性特点所赖以建立的心理基础,在于其接连不断地迅速变化而引起的精神生活的紧张。”研究城市社会学的德国学者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的开篇写道。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齐美尔经历了柏林从不足60万人的小城市,一跃成长为400万人的大都市的变化过程。或许是对这种紧 张感同身受,在这篇文章结尾,他说,“在我们转瞬即逝的生存中,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细胞,作为一个部分,指责与开脱都不是我们的事,我们能做的只是理解。”
余秋雨也看到了上海人性格与历史的复杂关系,他在《上海人》一文里写道: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周立波:上海人越来越从容
“现在的上海人不固执,能接受更多的新东西。”
周立波,1981年进入上海滑稽剧团,师从上海曲艺界暨滑稽界元老周柏春,成名于80年代末。2008年底,由周立波创作的海派清口《笑侃三十 年》《笑侃大上海》在上海引起了轰动。海派清口区别于依赖色情笑话的荤口,以幽默盘点时事,是一种带有浓郁海派特色的单人表演形式,其语言以上海话为主。深谙上海历史、挥洒海派智慧的周立波业已成为上海元素的代言人,人们称赞他:“充满笑声却处处蕴涵哲理的噱头,已不再是昔日的小市民滑稽,而进入了既适合 老上海人又使新上海人折服的大滑稽境界。”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海派清口”表演扎根于上海本土,主要受众也界定为“上海人”。在你心目中,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上海人”?
周立波:应该这样说,上海人的特点其实就是很难找到特点。上海人胆小、小气都是属于比较极端的说法,这都是对上海不是很了解的表现。我觉得上海确确实实可以说是海纳百川,它是一个多重性格可以融合在一起的城市。
不过无论是上海人还是新上海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每个人都有城市荣誉感,不管是过得好的、不好的,他们总会为自己是谁而感到骄傲。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表演里上海话和普通话开始平分秋色,是为了吸引“新上海人”吗?
周立波:我说普通话不是为了吸引“新上海人”,而是应该这样说:上海话的韵味和精妙之处是普通话所无法替代的,但上海方言语言上的局限性又需要普通话来补充。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界定“新上海人”?
周立波:就我自己来说,我家里是从爷爷辈就到上海来的,应该算是老“新上海人”。现在真正的上海本地人也并没有多少。我给“新上海人”的解释是,在上海有事业、有工作,能够接受这个城市的文化、并且能够融入这个城市的文化。
这群人是上海的新鲜血液,他们在这里干事业、结婚、生孩子,他们的下一代就会彻底融入上海,成为上海人,就像我的祖辈一样,只不过他们更优秀了。对他们来说,这里是一个有梦想的地方。所以说这里还是一个可以聚得拢人的地方,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像这里一样。
中国新闻周刊:除此之外,他们在性格方面是否有一些新的特点?(有很多外地人在上海工作、融入上海,但与人们印象里那种精明、讲究的上海人形象 大有不同)
周立波:我身边的朋友倒都是比较讲究的。北方朋友会认为上海男人喷香水、一丝不苟有点娘儿们,不爷儿们。我在微博 (http://t.sina.com.cn)里面写,“男人一丝不苟的吸引力仅次于女人的一丝不挂。”我是在调侃,女人有爱美的权利,男人也应该有。比较稳定的高收入人群或者有高学历的话,男人应该是会对自己的仪表比较注重,这不奇怪。
地域差别是永恒的话题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你的表演有时是靠调侃外地人来撩动上海人的优越感,但是那些被你拿来调侃的外地人正在对你咬牙切齿。造成这样的后果,你担心么?
周立波:我从来不担心,因为我没有恶意。他们对文化内核可能理解得比较片面。地域差别是永恒的话题,这么多年来,(调侃)外地人的话上海好像就 我一个人出来说说吧,而央视啊、巩汉林啊等等,(说上海人)说了十几年了,上海人也没见得不高兴,他们就会觉得“这是玩笑”,一笑而过。但有的北方的朋友,他们比较脆弱,真的。其实就是个玩笑,但他们会想:“你看不起我”。他们内心不够强大。如果胸襟是宽广的人,你会去享受这种调侃;而如果自己自卑的, 他们自己就会对号入座。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想过你的表演很可能会加深上海人和外地人的分歧和对峙么?
周立波:不会。我觉得只会加深彼此的了解。因为我在演出当中,一直在说一些南北差异所导致的误会。
由于地理、文化背景,包括饮食习惯的不同,北京人和上海人的性格完全是不同的。上海人习惯“以小见大”,而北京人多是“抓大放小”。但如果你理解了就会通融了,“以小见大”和“抓大放小”如果能够一直走下去的话,结果一定是殊途同归的。
反过来说,这次我到北京“解读”交响乐,非常感动。从幽默感的接受程度而言,北京观众要大大好于我们上海观众,到那里演出,难度比上海低。北京人比较喜欢开玩笑,他们都有幽默感。
世博会能让上海人的气质更丰满
中国新闻周刊:有一篇文章说,你要做的不是改变全国人民对上海人的看法,而是让上海人找到自己的归属感,你是这么想的么?
周立波:不是。无论是昨天、现在或是明天,上海永远是受关注、受瞩目的,这是不争的事实。我只是希望能以我的方式,让上海人能比过去更幽默一点、更豁达一点。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都对这次世博会抱有很高的期待,你觉得世博会能达到让上海人气质重造、脱胎换骨这样的效果么?
周立波:世博会必将会提升上海的城市气质。每个城市都会有自己的气质,从老上海开埠时起,上海就有它独特的气质。现在不存在“气质重造”的问题,但是世博会无疑能让它的气质更加丰满。
世博会就好比是北京的奥运会一样,对整座城市今后的发展一定会有好处。我觉得世博会以后上海的马路上应该会有更多的笑脸。
中国新闻周刊:能否具体谈谈上海人的变化?
周立波:最近一两年来,上海人给我的感觉是越来越从容,而且我感觉得到这里的中产阶层已经慢慢地形成,并且正在壮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表演是在重新为上海人定位。我说过上海人好的、不好的东西;会说他们爱听的,也会说他们不爱听的。比方说我有时候说上海人爱管闲事,有的上海人爱穿睡衣到马路上溜达。我们小时候也曾经穿睡衣上马路的,但是现在都知道,这个不礼貌。我在微博上也说过,“睡衣是睡觉时穿的衣 服,大衣是穿在西装外的衣服,如果你愿意穿着大衣睡觉,那么我们就理解你穿着睡衣上街。”
(完) |